《虽有千人仆倒》第17章
- 《虽有千人仆倒》
- 2016-12-18
- 2398

当卡尔,威利,埃里克和弗兰兹开车经过战俘营的大门时,他们为自己的好运欢呼了,因为是落在人道主义的美国人手里。
“我呆在卡车上,”弗兰兹对其他三个人说。“你们几个去找找其他的轻工兵营员吧。”
“主啊,”他祷告着,嘈杂忙乱的战俘营景象从挡风玻璃前过去,“你兑现了你的应许!惟有你配得赞美与称谢,在战争的诸多危难中你保守了我的性命。我将永不忘记你的慈爱。”然后他在卡车的后座里翻找,从一个箱子里取出军队的兵役记录,开始算帐,合上帐簿。
“注意!注意!”第二天早上喇叭发出响亮的声音,召集轻工兵营所在的营排队点名。来了几个分队,但没有找到整个第四分队,他们被认定已死亡。
也不是所有的轻工兵营都来营里了。麦尔克司上尉告诉剩下的人当天晚上吃完饭后到弗兰兹的营房里。弗兰兹给了每个人应得的最后一笔兵役金,兵役簿里记录了他们的资料。
“威利,你看,”他说。“所有的人都饿了。美国人没东西给这么多士兵们准备吃的。你能不能再为我们队做一次饭?”
“好主意,”威利说,第二天他从战俘营的厨房里带回了蔬菜和土豆,把这些都合在一起煮成浓汤,再把他们从罗马尼亚一路带回的面粉做成煎饼一起吃。
与此同时,弗兰兹到了营里的出纳员那里,上交了会计记录和剩下的钱,从那里收了张收据。他忠心而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然后他和卡尔把其他物资分给了大家:糖,向日葵籽油,够分每人满满一箱的香烟。
“请注意!”一个星期后,喇叭又响了。“所有要回法兰克福的人报上来,以便遣散释放!所有要回法兰克福的人,请马上报上来!”
“卡尔,”弗兰兹说,“我还没走。我不久就可以看到那片瓦砾地了,想先把这里的事做好。再说我还没打包呢。今晚我要把东西整理一下,下次就可以准备好了。”卡尔,威利和埃里克也决定留下来。
晚饭以后,弗兰兹仔细地把他的东西都摆了出来。除了食物以外,他还有一条崭新的裤子和新靴子,是从罗马尼亚买的——“这是我要离开时的衣服,”他告诉其他人。然后把自己的东西都收拾到背包,餐袋和衣袋里。在这些包裹上他缝了一个盖儿,来放装着5加仑向日葵籽油的罐子,这样只露出把手。打包好后,他的行李有150磅重。
两天以后,喇叭又响了,传唤那些要回法兰克福的人。四个朋友跑去向麦尔克司上尉道别,作为高级军官他必须被留下。然后他们带上东西,开始徒步走5公里到遣散中心去。
只走了一小段路,弗兰兹停了下来。他直喘气,大颗汗水从脸上滚落下来。
“朋友们,我们这样是走不到的。卡尔,跑回去,把我们营里的自行车借来。我们可以过后再还。”
卡尔很快回来了。他们把背包挂在车把上,把衣袋吊在车架上,再把油罐绑在窄窄的后座篮上。弗兰兹牵车,卡尔推着,其他两个人就扶着,保持平衡。现在他们快多了。其他士兵发现行李太重,就把大多数东西留在后面。
最后他们到了遣散营。一个德国的市长通过一只扩音器命令每个人填表。当他看到这四个人带着自行车时,大声叫道,“你们用自行车在做什么?不是要排队吗?”他们很快把车子放到地上,集合起来。然后他大吼着,“所有党卫军成员,到左边去。”有几个人走了出来,由一个士兵护送着到送回战俘总营去。剩下的上了一列火车,那里建有遣散中心。
在第一节车厢里,一个医生正在做体检。他们脱了衣服,他就给他们量血压,听听他们的心脏和肺。最后他对每个人说,“举起右臂。好的。举起左臂。好的。你可以去穿衣服了。”
弗兰兹对此完全不理解,其他人照例这么做时他很好奇地看着。当轮到埃里克中士举起手臂时,弗兰兹注意到在他臂下面纹了一个数字。
“啊哈,”那个医生说,“我们抓到一个了!党卫军的人不能被遣散走。请到外面等候。”
“埃里克,”当这四个人又聚到自行车前时,弗兰兹问道。“埃里克,我从来都不知道你是党卫军的成员。你根本不是纳粹的支持者呀。怎么了?
“埃里克叹了口气。“我在战争前几年加入党卫军的,”他说,“但那时我很失望就退了。战争开始时,我自愿加入普通军队。我想我要回战俘总营去了,我去还自行车。”朋友们难过地道了别。
弗兰兹,卡尔和威利带着他们的遣散单到了下一个车厢,进行最后批准。
“注意站好了,”桌子后面那个美军上校说。
大家站直了。卡尔一直都是希特勒的强烈反对者,这时他却出于习惯伸出右臂说,“万岁,希特勒!”
上校盯着他,被吓了一跳且非常厌恶。“拒绝释放!”他叫着。
“现在,”他转向弗兰兹说。“把你的单子给我。”他浏览了一遍,用流利的德语说,“我看到你的兵役记录里有一条,说战后你要被送到军事法庭去。”
“是的,长官。”弗兰兹已经仔细看清了这个出口。
“你做了什么?”
“我因信仰的缘故拒绝了一项命令。我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教友,按着圣经的教导守安息圣日。有一次,在休息的日子里突来袭击。我拒绝执行任务,因为那天是安息日。”
“等一下。”上校的眉头和音调都显明了他的愕然与怀疑。“你不是说真的吧。整个战争中,你在纳粹军队里守安息日,而且还活着?”
“是的,长官。上帝保守了我,即使是在德国军队里。”
“真是奇迹。”上校说。“顺便说一下,我自己是个犹太人。但即使是在美国军队里,我也没有守安息日,因为太难了。”
“上校,”弗兰兹勇敢地说,“我建议您要守安息日。”
“我想我是应该这么做,”那个人说。他仍然惊奇地摇摇头,继续问问题。“你的职业是什么?”
“我是做福音工作的,是个书报员,上门销售信仰书籍。”
“很抱歉,我们这时候只允许释放在农场工作的人。你懂得一点儿耕地吗?”
“嗯,从6岁到14岁,我和祖父住在一起。他是个农民,住在德国南方。我知道所有的农活。”
上校摇摇头。“那样不行。太早了,不是现在的。”忽然他想到了,“嗨,你有没有什么园子之类的?”
“是的,我们在法兰克福有个小菜园。”
“那就是了!”他在一张单子上草草地签了几个字。“我现在释放你,去主的葡萄园工作吧!”他愉快地笑笑,把单子交给了弗兰兹。
他在上面写的是“农业督察员(Agricultural Inspector)”
很快,美国的卡车就到了。弗兰兹是第一个上车的,威利把他们的行李送上去时,他很快地塞到座位下面,这样就不会占用太多地方了。他们上路了:布劳瑙(Braunau), 雷根斯堡(Regensburg),纽伦堡(Nuernberg),法兰克福。他们得知每过几天,就有一卡车车队开往卢森堡(Luxembourg),运送食物到战俘营。回来的时候,卡车就运送被释放的战俘。两个司机轮流开,24小时后就到了法兰克福。他们在市郊下了车。
那是1945年5月21日。弗兰兹自由了。
原来的营队有1200名轻工兵营队员,只有7人生还;其中只有3人没有受伤。弗兰兹哈瑟,这个佩带木头手枪的人,是这三个人之一。
差不多两个星期前,伊思臣罗教堂的钟声拼命作响,把海伦吵醒了。她听到门外人们在跑着,叫着。斯多尔伯先生敲着她的门,大声叫着,“哈瑟太太,哈瑟太太,快下来!”
海伦飞快地穿好衣服,跑了出来。她看到在大街上德国人和美国人笑着,哭着,互相拥抱着。那是在1945年5月8日。战争结束了。村民们被告之希特勒已经自杀,德国投降了,同盟军把德国分成四块。伊思臣罗是美国管辖区,在新政府成立前,他们要服从美国的治理。在新命令发布前,所有从城市里来的疏散人员不得回家。
“孩子们,孩子们,到房子里来,”海伦把他们叫来。这个小家庭回到他们的房间里,感恩地跪下来,感谢上帝在战争中平安保守了他们。
“但是爸爸在哪里呢?”祷告结束后,洛蒂轻声问。“他还活着吗?”
“上帝啊,求你,”海伦祷告着,“把他带回到我们这里。”
一天一天,一个星期一个星期都缓缓过去了。自战争的最后一周以来,这里变化都不大,除了一点:燃烧的法兰克福市在夜间不再发出橙红色的光了。
孩子们去上学,并到田里帮忙,因为只剩很少能干活的人了。好久好久都没有爸爸的一点消息。他最后一封信是在苏联的高加索山寄来的,有人悄悄地说:在那里被抓到的德军已经被送到西伯利亚劳改营去了。
在法兰克福的郊区,弗兰兹和威利望着那堆放在路旁的行李。
“威利,我们根本扛不动这些。”年长的他说。“你呆在这里看着,我去找东西拉。”
弗兰兹非常震惊地看着这个被破坏的城市。他不久后得知法兰克福80%被夷为平地。到处都是女人们在碎石堆里挖着,想找还能用的器具。一个男孩子正把砖头上的灰浆敲下,这样就可以重新利用起来。
弗兰兹看到一个老人正拉着一辆木头的手推车,他走了过去。那正是他所需要的。
“对不起,请问那是您的车吗?”
“是的。”
“我们刚从战俘营被释放回来,有很多东西。如果您可以把车子借给我们,我就任您选一样,或是100马克,或是5镑的烟草,或是半升的向日葵籽油。我们过几天就把车子还给您。”
那个人仔细看看他。“嗯,我正从火车站来要回家去。我在那里发现了些煤——你知道我的意思吧。”
“没问题,”弗兰兹回答说。“我会跟您一起回家,帮您一起把煤卸下来。”
“好的(Jawohl),”那人同意了。“顺便说一下,我想要油。”
那个人从没问过弗兰兹的名字或住的地方,但乐意地把车子借给了他。弗兰兹带着车子回到威利那里,他们把行李都装上车,在上面盖了布罩免得人注意。然后,他们又是推又是拉地经过了碎石满地的路。
“哦,哦,”威利说。“我知道我们不会有好日子了。”
“为什么?”
“看是谁过来了——太太们。”
女人们看到士兵就从各个方向拥了过来。她们瘦弱的身体和破烂的衣服都说明了在国内战争的破坏性。她们静静地看着,眼睛里充满希望和害怕。
然后就开始问问题。
“你们从哪里过来的?”
“我们从东线过来。”威利说。
“我的丈夫也在那里,”一个女人说,其他人也附和着,问着各自的问题,一个名字接着一个名字地问。“你们有没见过Georg Schneider?你们有没有Heinrich Gerber的消息?”
“女士们,想想吧,”那两个人回答说,“我们不可能知道所有到苏联打战的人哪。”
弗兰兹转向威利。“如果这不停止的话,我们永远也到不了家的。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说,我们刚从奥地利回来。”
又一个女人朝他们走来。
“你们从哪里过来的?”
“我们刚从奥地利过来。”
“我最小的孩子,Hans Kimmel在那里。我好几个月都没他的消息了。我其他三个孩子死在苏联。你们有没知道什么消息?”
“没有,很抱歉。我们没听过那个名字。不知道什么消息。”
“弗兰兹,这样也不行,”威利说。“我们就说刚刚从战俘营里回来吧。”
美国兵驻扎在他们要过的每一座桥头。他们每一次都要出示放行单子。文件没有问题,但美国人怀疑地看着车子。然而,没有人拒绝放行。
又一个女人跑着追他们。
“你们从哪里过来的?”
“我们刚刚从战俘营里被放回来的。”
“你们是哪个营的?”
“轻工兵营699。”
“我丈夫也在那里。你们知道Ludwig Keller吗?”
“Keller太太,”弗兰兹说,“你的丈夫和我们坐同一辆卡车回来。他可能已经到了,站在你们家门口进不去呢!”
那个女人欢喜地叫了起来,转身就跑了。
“威利,”过了一会儿,弗兰兹说,“我们一起先去我家吧。虽然还要穿过镇子才到,但比你家要近。”
“太好了,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傍晚的时候,他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看着城市一排一排被夷为平地,当看到街区里6座高大的公寓楼还完好无损时,真是一种震撼。它们像个巨大的屏障,矗立在碎石瓦砾之上。
弗兰兹和威利把车子推进去时,一个邻居探出头来。
“哈瑟先生,你回来了!欢迎,一千个欢迎!你是第一批回来的人。”
“Jaechel太太,真高兴见到您。”
“你的家人不在这里。他们在伊思臣罗。”
弗兰兹一时搞糊涂了。“伊思臣罗?”
“你知道的。在福格尔斯贝格山里的那个村子。”
他点点头,叹了口气。“非常谢谢您。祝您愉快。”
弗兰兹拿钥匙开了门,战争年间他一直保管着。他和威利把车上的东西卸下来,威利洗澡的时候,弗兰兹检查了他的房子。窗子破了,窗帘飘荡在风中,但东西都没少。家具,床单,碗碟,书,甚至弗兰兹在战前的摩托车也停放在空房间里——东西都在。不久后弗兰兹得知波兰的战俘住在离这里1/4英里远的小学里,他们被释放后就到处抢劫,把所有没固定住的东西都拿了。上帝显然伸出手在哈瑟家的房子以上。
最后弗兰兹洗了个澡,刮了胡子,他们吃过饭后就休息了。哦,能再回到自己的床上睡觉真是太好了!
第二天,两个朋友道了别,威利往他在陶努斯(Taunus,注:是莱茵片岩山的东南部分)山中的家走去,把一半的行李留在哈瑟家以后再带。
弗兰兹得知他的家人在那遥远的村子里大概很安全,他走了8英里到市里的区会报到。区会主席出来欢迎他。
“哈瑟弟兄,你是战场回来的第一个区会工人!”他解释着,“你可以帮忙我们做一段时间牧师吗?我们现在非常缺乏,因为许多工人都丧生了。目前还没有出版工作。事实上,我们连出版社在不在还不清楚,因为没有火车,没有邮件,没有电话。”
“我说,”弗兰兹说。“如果上帝需要我做牧师的话,我就会做的。但我的家人不在这里。我已经很久很久没见到他们了。让我去把他们带回来,我会准备好从7月1日开始。”
“哦,哈瑟弟兄,你真不知道我有多感恩。上帝保佑你!”
第二天弗兰兹把手推车还给了物主,还有承诺的油。他开始走40英里的路去伊思臣罗。路没完没了地延伸着。他在一个仓房里睡了一晚上,然后继续走。
最后他看到一个路标“伊思臣罗:5公里”。弗兰兹在树林里的溪水旁停了下来,把自己整理干净,刮了胡子。他听到有货车的声音从路上经过,就向司机打招呼。
“嗨,你是要去伊思臣罗吗?”
司机点点头。“我住在那里。”
“我刚从战场回来,”弗兰兹说。“我妻子被疏散到那里。你知道有个哈瑟太太吗?”
“哦,是的,她住在村长家里。来吧,”司机说着,爬下车来。“把你的包放在车上。地方太小了,不够我们两个坐,我就和你一起走路吧。”
离村子还有一段路时,弗兰兹看到有个男孩子从泥泞的路上走过来。那孩子遮着太阳,朝他们这里望着。忽然,他开始跑过来。
“爸爸!”他大声叫起来。“爸爸!你回来了!”他扑到爸爸怀里。
“杰德?”弗兰兹声音颤抖着。“真是我的小杰德吗?”
“哦,我真是太高兴了!”杰德喘着气。“我每天一直在这条路上走,希望第一个见到你!哦,爸爸!”
司机笑了。“跳上车来,孩子,”他说。“我想我最好上来坐你旁边,让你不跟马车一起跑。”
“我走路吧,”弗兰兹说。“我坐不住的。”
在凉爽五月的一个下午,海伦坐在农舍外面粗雕的长凳上剥花生壳。两个大点的孩子在外面玩,小苏茜在一盆水里漂着花生壳。
她远远看见邻居从集市上回来了,坐在两匹马拉的货车上。一个身材高大,晒得很黑的人跟在后面。海伦不认识他,想着他要朝哪里走。就在那时她看到杰德坐在邻居的车上,骄傲地笑着。
他们过来的时候,马车停了下来,那个邻居喊着,“哈瑟太太,我带了个客人给你。希望你能高兴。”
海伦有点点惊讶地回答,“你带了杰德一程真好。”
这时那高高的陌生人赶上来了,从货车上卸下包裹。海伦盯着他深棕色的脸,他走近了。然后他开始笑,海伦认出来了。
“孩子们!”她高兴地屏住呼吸大声叫起来。“孩子们!快来呀!太好啦,爸爸回来了。爸爸回来了!”
6年的战争与离别,哈瑟一家又团聚在了一起。
本文由【#领受这道网站】首发,转载须告知。
本文链接:http://muyisheng.com/index.php/post/286.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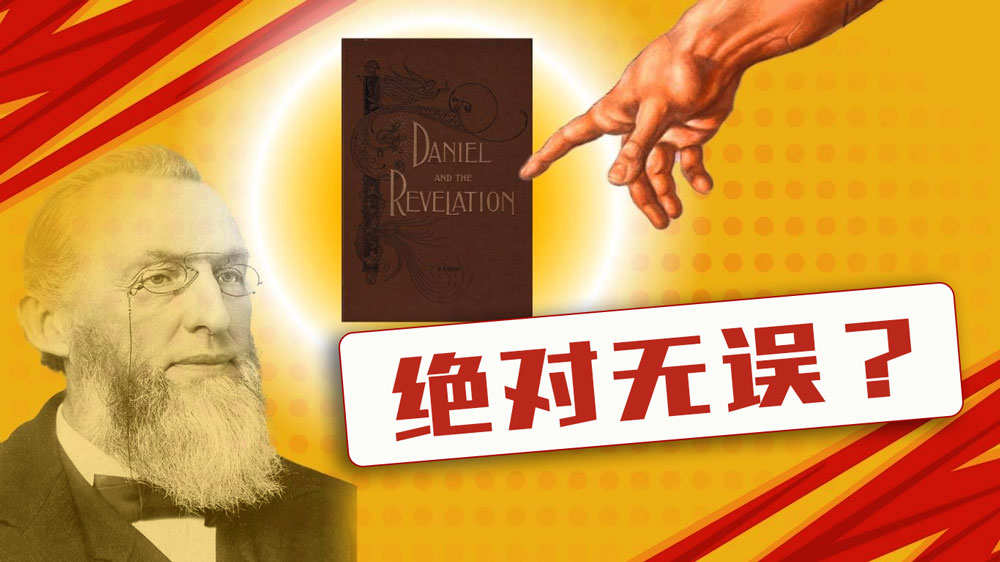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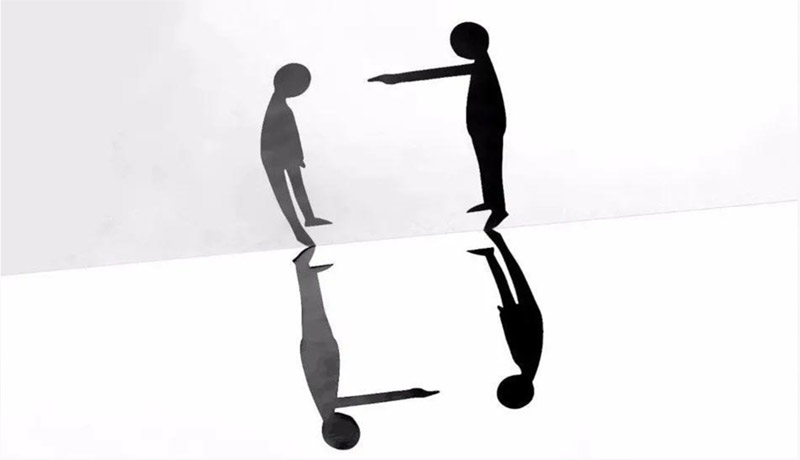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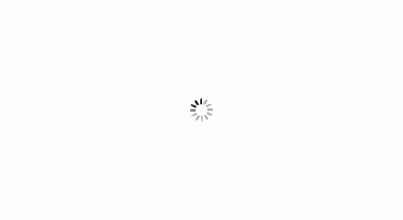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