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有千人仆倒》第13章
- 《虽有千人仆倒》
- 2016-12-18
- 2060

在伊思臣罗过了几个月,海伦和孩子们想念自己家的自由和舒适了。
“妈妈,我们回家吧,好嘛好嘛!”孩子们乞求着。“我们想见表哥表姐,还有我们的朋友们。上帝可以在那里也保守我们,像在这里一样!”最后,海伦同意了。他们很快把东西都打包好了,把它们堆放在他们的三辆小车子上:一辆破旧的黑色自行车,婴儿车,还有一辆幼儿车。
他们一早就起程。这次他们无法再坐火车了,因为大部分的铁路都被炸毁了;他们要步行40英里。
“你们要去哪里?”路上人们问道。
“法兰克福。”
“你们到不了的,”人们说。“所有的路都被坦克堵着。”
海伦礼貌地点点头,但她心里想,即使有1000辆坦克堵在路上,我也要带孩子们回家。主若与我们同在,就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他们稳步走了几英里,上山又下山。两个男孩子轮流骑那满载的自行车,洛蒂推着幼儿车,海伦跟在后面推着婴儿车。天越来越热,他们也越走越累。最后,他们开始上一个坡很长的山,洛蒂没力气了。海伦叫着儿子,杰德跑过来了。
“来,”当他看到姐姐的状况时说,“把那个给我。”他双手抓着小车的扶手,用力继续把它推上了坡,洛蒂就紧紧靠着海伦推着的婴儿车。他们在山顶上休息。
海伦指着山下。“看,”她说,“我看见那下面有座房子。如果我们可以走到那里,就可以吃点喝点东西,感觉就会好多了。”
孩子们受了鼓舞,继续前进。当他们到达那房子时,有个女人探出窗外,静静地看着他们走近。
海伦向她打招呼。“我们正要去法兰克福。我有4个孩子。您可以给我们一些吃喝的吗?我们非常感谢您。”
当他们在一棵苹果树阴下休息时,那个女人回来了,只拿着一大壶的水。“喝吧,”她说,“然后走吧。我不希望有流浪者在我家附近闲荡!”
海伦快要哭了。他们喝了很久——甚至小宝宝苏茜也喝了水。然后他们继续走下了尘土飞扬的路。当夜幕降临时,他们爬进一个空草房睡在那里。
第二天早上,他们又饿又累地继续前进。他们很快就筋疲力尽了。太阳从天空中烤着大地,热汗像水流一样从他们身上流下来。海伦的心脏跳得好象要破裂了,她不得不竭力呼吸。洛蒂的脸涨得发青。海伦怕她中暑了,就让她在路边一个麦田的阴凉处躺下,轻轻和她说着话,用一把凉草擦她的脸。
“别难过,”她说,“我们再往前走点,就可以找到另一座房子。我们就能在那里的阴凉处休息了。洛蒂,勇敢一点。上帝会照顾我们的。我们继续往前走一点吧。”他们站起来,继续忍受着酷暑,走那看不到尽头的路。
最后,洛蒂叫起来。“妈妈,妈妈,我看到一座房子了!”
他们走近时,一个女人出来了。她看了看他们——海伦的心缩了一下,等着又一次的拒绝。但这个女人则不同。
“你们跟我来,进到门里面,”她说,拉过婴儿车。“在阴凉处休息一会儿,我去给你们拿点吃的来。”很快她带着胡椒薄荷凉茶回来了,然后是一份丰盛的素汤,还有几大片的农场面包,这些东西连苏茜都可以吃。很快这一小家人就感觉恢复体力了,继续向前走。
那天晚上,他们在远处望见离他们家不远的一座水塔。海伦知道那儿从8:00起宵禁,8:00以后就没有人可以外出到大街上。我们赶不及了,海伦想着。但是他们继续往前走,武装卫兵看到他们疲惫邋遢的样子,挥手让他们过去了。
他们转到他们的街道里,看到了房子。它还在那儿呢,海伦惊奇极了,真是奇迹,它还立在那里呢。窗户又都震破了,但没关系。他们回到家了——回家了。
“妈妈,”孩子们祈求着,“让我们都呆在这里,永远不要再离开了好不好?”
“嗯,我保证。”海伦叹了口气。为自己的缘故,也为孩子们的缘故,她绝望地希望可以信守这个承诺。
但是秋天来临,尔后是冬天,她开始考虑是不是可以守住这个承诺了。食物比以往时候更少了。现在,报纸除了登载死亡的士兵外,也登载了因饥饿而死之人的名单。旅行也被禁止了。他们想见住在法兰克福市中心的安妮姑妈和她的两个孩子,还要去警察局申请批准,但常常被拒批。但他们发现纳粹党员都可以自由走动。
当然,最重要还是食物。每天深夜,海伦都叫醒库特。他睡得很沉,跌跌撞撞地爬出了床,用蓝紫色的僵硬的手指套上几件衣服,最后穿上他那脚趾开了口的鞋子。和其他孩子一样,他已经长大穿不下了——要等到春天才可以得到另一双——所以海伦把脚趾头部分剪开,好让继续长长的脚可以放进来。
他喝下一杯热腾腾的用烤谷物做成的代用咖啡,走出临时的地下卧室,在黑夜里出门了。他立起衣领,把手深深插在大衣口袋里,低着头向刺骨的风挺进,走过几条街站在等面包的队伍里排队。其他几个单独的身影,黑暗而孤独,也从镇上的其他地方过来了。最后他们到了目的地——面包店门口的队伍中,有时候20个人,有时候50人,都又忍着寒冷又安静地等着他们每天的配给面包。
两个小时后,睡意惺忪的杰德来换下哥哥,库特就回家穿着衣服就爬上床,希望可以暖和些继续睡觉。洛蒂等下再来换杰德,幸运的时候面包就在她排队时等到。如果延迟的话,库特就再轮一班。通常拿着面包的孩子到家时,一头就已经被吃掉了。海伦不忍心责骂饥饿的孩子们。
冰冷的冬天终于过去,又一个春天来临了。海伦尽快在他们园子的地里一个被保护着的阳光充足的地方种下菠菜。菠菜很快就发芽了。孩子们知道这是给小宝宝留着的,她非常需要营养。
一天早上洛蒂从等面包的轮班中哭着回家了。她坐在厨房的餐桌旁,仍穿着那磨损的旧大衣。她的手腕因寒冷而擦痛,袖子已经太短遮不到那里了。
“怎么了?”
“一些大孩子把我推出了队伍中,”她抽泣着。“我就又得排到最后面。当最终到我时,面包都没了。我好饿呀!”
“我们还有一点点米,”海伦安慰着说。“我们没事的,明天吧。”
一会儿,她去园子里摘些菠菜给苏茜吃,但发现那一小块地已经被摘得干干净净了。她沮丧地回来,要孩子们解释。库特承认把菠菜吃了。海伦能做什么呢?他们都在挨饿着。
一天他们家来了意外的客人。爸爸的姐姐,安妮姑妈和她的丈夫,费利兹(Fritz)姑丈站在门外。费利兹姑丈回来休假。他应征去了布雷斯劳(Breslau)当高射炮兵,他告诉家人那里的战争太可怕了。
“我不知道还行不行。”他最终说。
他们在一起祷告,几天以后他又回岗了。那是他们最后一次见到他。布雷斯劳的德国兵力完全被扫清,没有生还者。费利兹姑丈被列在战争失踪者中。
又过了不久,安妮姑妈和表哥表姐安妮丽斯和赫伯特又站在门口。前一天晚上当他们躲在地堡的时候,他们在法兰克福市中心的房子被完全炸毁了。他们和哈瑟一家一起住了几天,然后就被疏散到莱茵河上的一个小镇子去。恐惧将不会结束了吗?
一个14岁的女孩子被选派到海伦那里帮她做家务。希特勒下令小学毕业后,所有的女孩子都要免费工作一年,作为对战争的一种效力。塞克莱(Thekla)是个不被家庭接纳的私生女,她很高兴和海伦呆在一起,海伦待她非常好。但是,塞克莱不知道要怎么照顾小宝宝,还有料理家务。海伦就耐心地教了她一些必要的东西。塞克莱非常依恋着这家人,战后还常常来看望他们。
和往常一样,孩子们在安息日去教堂,而没有去学校,这让所有的老师都不喜欢。杰德的数学老师纽曼先生(Herr Neumann)特别不喜欢他的这个小学生。
“哈瑟,”他严厉地说,“你在蔑视我。你拒绝用“万岁,希特勒”的问候礼,还有你在星期六没来上学。但我知道怎么做对你最好!”
纽曼先生安排了他的课程,这样星期六这天他总是讲授新的数学概念。然后每一个星期一早上,他就从包里拿出红色的年级点名册,打开,看着几排名单,然后叫杰德来黑板前做新题目。头两次,杰德又难为情又害怕,无助地站在黑板前看老师把不及格的标记,一个大大的“6”填在红册子上,他的同学们就在下面偷偷地笑。
最后他接受了事实,库特和洛蒂也是这样过来的。星期天时,这三个孩子就跑到同学们的家里,问前一天老师教了什么内容,还有星期一的家庭作业。由于杰德的同学们没几个对数学感兴趣,他常常会得到3,4个不同的版本。但回家后,他就拿出数学书,自己研究那些问题,直到把概念掌握下来。
这个一点点也不开心的纽曼先生也对另外两个男孩子很不满,不失时机地羞辱他们,把他们记在那讨厌的红册子上。
“我们一起来报复他吧,”他们说。于是这三个孩子一起等待着时机。最后一天,他们有机会了。
“纽曼先生把点名册留在他讲台上了!”
两个孩子守着,还有一个就爬进教室,把它拿了出来。
“我们要怎么办呢?”
稍微争论了会儿,他们决定要以破坏行为来庆祝。他们分了工,商量半个小时后在尼塔河岸碰头。
在那里他们开始行动了。他们首先翻了几页,重新核对了年级。他们看到自己名字的后面都是长长的“6”,而其他学生的成绩都是1或2。
“我受够了,”一个说,“都准备好了吗?”
他们把这个册子放在一个破碗里,泼上汽油,放到水里。他们站在后面,划了一根火柴,把它丢在碗里。册子烧着了,一个人用脚轻轻碰了碰碗,他们高兴地看着河水把这个讨厌的红册子冲到下游去了。
同时,多凌先生也重整了他的侵扰行动。海伦很快收到学校的又一封信。即使是在开信前她也知道是为何事。她对新校长解释了她的情况。
“哈瑟太太,”他回答说,“你和你的家人被指控为化了装的犹太人。我命令你星期六送孩子们来学校!”
海伦曾经历过这些,她非常坚定。“我的孩子们不会来的,”她说,“你对此什么也做不了。上帝会顾念我们。”
他双手张开,拍着案头。“我们走着瞧。”他嘶声说。
海伦回到家,把这个熟悉的消息告诉给了沮丧的孩子们。
“哦,妈妈,”洛蒂哭着说,“孩子们总是在取笑我。他们太坏了。现在是越来越糟糕了。”
“别怕,”海伦安慰着,“上帝有千千万万的天使来保守我们平安。祂会施行神迹的。”
安息日早上,一家人跪着祷告。他们还没站起身来的时候,空袭警报响了。
“轰炸机来了,”洛蒂说。
库特的眼睛瞪得大了。“为什么他们会在白天来呢?我们的高射炮很容易就会把它们打下来的呀。”接着他就兴奋地叫着,“妈妈,那意味着不要上学了!空袭时学校就放学呀!”
从那时候起一直到战争结束,在法兰克福夜间不停的空袭中,非常明显地每一个安息日早上也都有场空袭。
寇勒阿姨(Tante Koehler)是个忠诚的复临信徒,也是海伦的一个朋友。她唯一的儿子说了反对政府的话被拘留,被驱逐到达豪集中营(Dachau,注:德国第一个纳粹集中营)里去。不同于政策的是,她曾被允准到那里看望了儿子一次,因此成了少数知道在死亡集中营里残暴之事的人之一。
她懂得一点儿英语,晚上的时候她常会偷偷地把她的小收音机放在床头,听敌台广播的新闻,如果被发现的话她就会被处刑送往死亡集中营的。
德国的新闻自然是充满鼓吹号召,来尽量保持高昂的士气。“我们已经又赢得几场战争了!”报纸上呼喊着。“元首向东又前进了!”德国永远,永远都是赢的。
但是伦敦的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则不同。当寇勒阿姨来探访他们时,她和海伦总是在关闭的门后低声说话。事实是,同盟国无情地接连猛打德军,使他们从所有的战场往后撤退。
那不会持续太久了,海伦祷告着。亲爱的上帝,让战争停了吧,让战争停了吧。
现在,即使没听BBC的人也知道局势转变了。他们所做的就是抬头看看天空。每一天,敌方的飞机就像银色的鸟一样高高编队飞在空中,向未知的方向飞去。库特和杰德有一次只数了一队就有1,100架飞机。
晚上的时候总是有同样的事。首先是侦察机来,高高地飞着,到处寻找夜间的目标,然后丢下烧着的照明弹,把那地方照得像白天一样亮,然后它们就慢慢地下来。因为那些做标记的是个三角形,德国人给它们取了外号叫“圣诞树”。然后20队的轰炸机就隆隆飞过来了,同时丢下致死的炸弹,然后那地方就像铺上炸弹一样。
晚上的空袭警报一解除,海伦就跑出去看着夜晚的天空。她常常看到那耀眼的“圣诞树”监视着她那6层楼的公寓,可能是把那当成了20英里外德国的一个军队营地。
然后她常常就开始祷告。
“我们的天父,求你今晚上保守我们。你是刚强而有能力的。我知道你的天使正环绕在这些房子周围。求你保守我们平安。”
她看着,那些“圣诞树”就一个一个地熄灭了。轰炸机来的时候,他们的目标都看不到了,就随机地丢了炸弹。
海伦和孩子们缩在小小的地下室,在那样的恐怖中无法入睡,累极了。每天晚上他们都听到炸弹低鸣着,撞在地面嘶嘶作响,然后就是让大地都震动的爆炸,这样有几个小时之久。如果就撞在附近,整座楼都会震动,地板晃得像地震一样。气流震破了窗户,撞开了门。如果有人还没来得及到地下室,他们就会被猛冲下楼梯。榴霰弹的气味充满了空气中。轰炸没完没了。持续的危险,睡眠的缺少,还有寒冷都在刺激着每个人的神经。但整个战争下来,没有一颗炸弹直接打中这个6层楼的房子。
在特别紧密的空袭过后,库特和杰德就带着家里的木推车,走了5英里到市中心。他们要小心地绕过散落在街道上的碎片。常常会见到烧焦的尸体,缩到原来体形的1/3——那是空袭时逃出房子之人的尸体,被磷弹烧成的。
那些楼房在可怕的大火过后仍然冒着烟。两个男孩子小心地拉出横梁,门,窗架子,还有其他可以烧的东西。有时候他们会找到还没爆炸的地雷,就把它们放在一边继续走着。他们还没完全明白这东西的危险性,直到库特的一个同学握一枚手榴弹时被炸掉了手。当他们的小车子装满后就拖回家,让海伦用来取暖煮饭。
男孩子们最喜欢的就是在地面上找有形状的榴霰弹。那些是孩子们中最珍贵的东西了,可以用来换其他的宝贝。
多凌先生继续行动,要让海伦垮掉。他策谋了新的手段。库特差不多14岁了,要参加少年团(Jungvolk),那是希特勒为10 ~14岁的男孩子成立的组织。他们在那里学习生存技巧,参加社会交往,学唱爱国歌曲,还有劳力的体能练习。
也许那是我儿子在不违背原则前提下可以参加的。海伦想着。听起来无害且有益处。没必要的情况下何必去得罪纳粹党呢?
库特接受了这命令,去了入伍办。他填完表,就被发放了少年团的制服:一条棕褐色的裤子,一件褐色的四扣翻领衬衫,有两个胸袋,一只褐色的带帽舌的帽子,一条围在脖子上的棕色皮环的黑领巾,一条黑皮带——闪亮的皮带扣环上印着德国鹰抓着纳粹标志,周围刻着英勇的字“鲜血和荣誉”(Blood and Honor).
库特听着周围不停的谈论,他开始考虑这次入团究竟会有多无害处了。其他的男孩子骄傲地穿着制服,吹嘘着将来的大权局势,吹嘘着加入希特勒青年团(Hitler Youth)是如何获得晋升为希特勒精英部队党卫军的必要途径。也许对一个青年基督徒而言,那不是一个合宜的组织。
很快库特就被告之要在安息日当班。他静静地选择了呆在家里。那里有那么多的孩子,也许他们不会发现他没来。但他错了。
希特勒青年团的领袖还是个不成熟的17岁的少年,一天早上他来到了哈瑟家。
“哈瑟太太,”海伦开门的时候,他的口气极无礼地说,“库特在星期六无视公民义务。我这次来是命令他这星期六要做报告!”
海伦平静地看着他。“你不能要求我做什么,”她说道。“你不过比库特只大一点点而已。我是他的母亲,我来决定他要去哪里,而不是你。”
那个年轻人显然过去一直在观察他的上级们怎么做的,因为他所做的就和他们一样。他站直了。
“我要让你看看这里是谁在负责,”他大叫着。“我要向政党指控你。我们看看是谁是做主!”
“你要做就做吧。”海伦向他关了门。
他第二次见到库特时就嘶声叫着,“我想狠狠踢你一脚让你不能走路。你觉得你很了不起,很伟大是吗?我要收拾你!”
政党的反应非常迅速。库特接到一封亲手送到的信。他被征召入伍,要马上去前线。他被告之当天下午4:00要来报到。
当海伦读完那通告,她感觉有人在拍她的肩膀。当她转过头的时却没有人。她觉得是听到了有个声音在低声说,“快啊,快啊!你还在犹豫什么呢?”那个声音越来越急促了。
海伦马上知道要怎么做了。
“库特,”她说。“去拿自行车骑到伊思臣罗。这儿有一点面包。把它放在口袋里。”
“我可以在后面的口袋里多带一些食物吗?”
海伦摇摇头。“你不能随身带东西。不然邻居们会发现你是在逃走的。”
库特深深吸了一口气,对这些迅速的决定他有些糊涂了,他摇摇头。“你们怎么办呢?他们会来找你们的。”
“我会和孩子们跟后面走的。杰德?”
“我在,妈妈。”
“杰德,出去外面看看有没人在偷看。”
都准备好了,库特出了门,很快就不见了。
海伦匆匆检查了房子,收拾了一些最重要的东西,把它们小心地垫在婴儿车下面。她无法再多带了。看起来要像他们正照例带着小宝宝下午去散步的样子。她把苏茜放在车子里,把杰德和洛蒂聚在身边。
“就在这里呆一分钟。”她说,然后穿过楼梯到一家信得过的邻居门口。她轻轻地敲了敲门。
门开了一个小口子,然后开大了,那个女人把她拉了进来。
“我来又要和你说再见了,”海伦说。“我们要去乡下。无法告诉你是哪儿。”
那女人眨眨眼使了个眼神,“我理解。你们平安地去吧。如果有人问起我,我什么也不知道。我会留意下你的丈夫的。”
海伦感激地握握她的手。然后她和孩子们出去了。没人看见他们离开。
以后海伦从邻居那里得知那天下午发生的事。5:00时,希特勒青年团的领袖跟着多凌先生还有另一个政党官员来到了他们家。他们只找到一个关着的门。他们按了门铃,对着门又敲又踢。他们从窗户往里看没看见那里有人。
“你等着!”他们愤怒地叫着。“我们会找到你的。我们会回来把你从床上拉起来,你这个逃兵!最终你会得到应有的报应的!”
他们按了邻居家的门铃。
“哈瑟太太在家吗?”
“很抱歉,”她说实话,“我不知道她在哪里。你们有没按了她家的门铃?”
“我们今天晚上会回来抓库特——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就强行开门。”
那女人耸耸肩,又进去了。
他们半夜又来了。他们用力砸了一会儿哈瑟家的门,然后又按那邻居的门铃。她在等他们呢。
“我受够了!”她尖声叫着说。“现在是半夜。出去,让我安静一会儿!”她使劲关了门,上了双重锁。那些人又敲了其他家的门,但没人开。最后他们发怒地离开了。
海伦和孩子们一直在长途跋涉走着那熟悉的路。路没有尽头地延伸着。苏联的战俘向着同一个方向跋涉着,他们像骷髅似的,血淋淋的脚上裹着破布。当海伦停下来给孩子们吃的东西时,他们用渴望而空洞的眼神看着。海伦把她自己那份分了一半给其中一个人。他贪婪地全咽下去了。
他们继续走着,一个苏联年轻人,看着婴儿车。当他看到苏茜时,轻轻地摸摸她的小脸。他在车子旁边走了几英里,一直牵着小宝宝的手,眼泪从他那憔悴的脸上拼命流下来,滴落在路边的泥土里。海伦非常同情他。她想他是不是在家里自己也有这样的孩子。
两天后,他们尘土满面,又饥又累地到了伊思臣罗。宙斯特一家没料到还会见到他们,已经收留了其他的疏散人口。但是村长斯多尔伯先生(Herr Straub)同意给他们提供住的地方。他们躺在床上,心想着这里等着他们的会是什么呢。
本文由【#领受这道网站】首发,转载须告知。
本文链接:http://muyisheng.com/index.php/post/282.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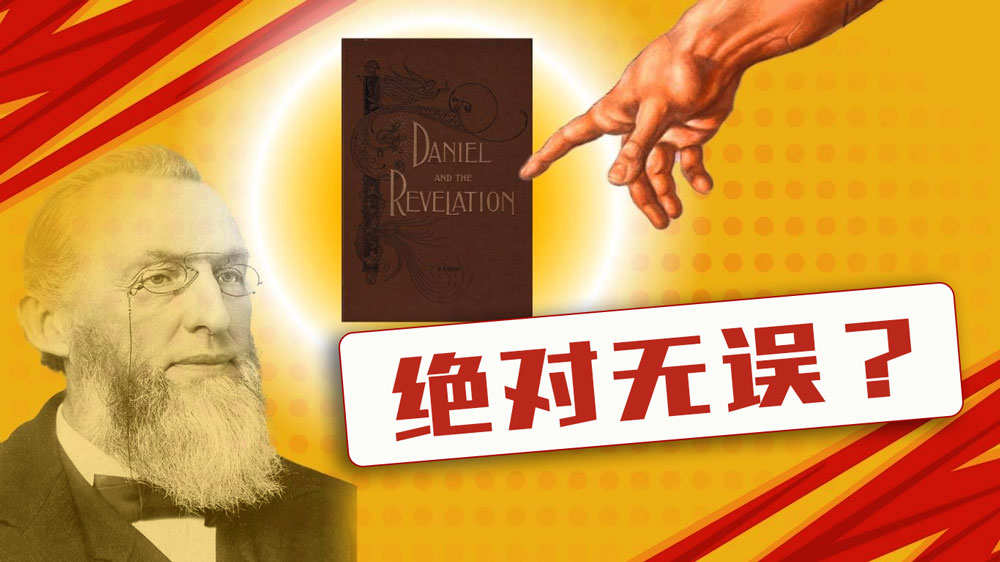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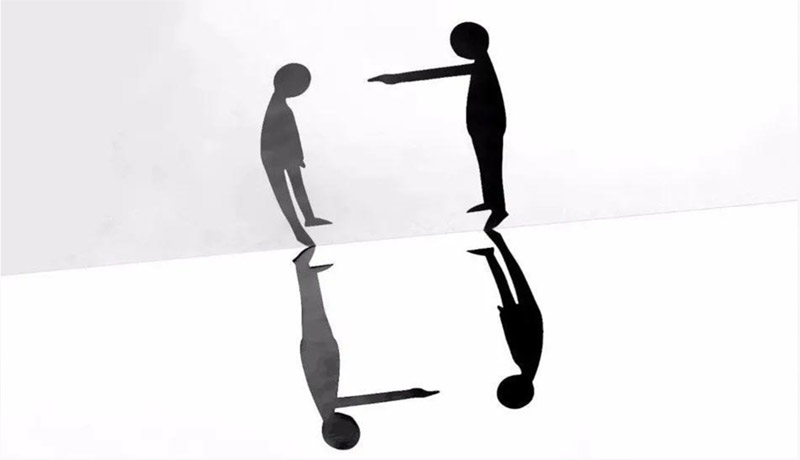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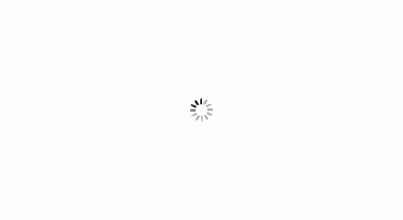


发表评论